-
2023-11-20
-
2023-11-13
-
2023-11-11
-
2023-11-08
-
2023-11-08
邓紫棋_邓声国:清后期《仪礼》学的传播与接受
更新时间:2021-08-04 来源:结婚祝福语 点击:
【www.xushengjz.com--结婚祝福语】
由内容质量、互动评论、分享传播等多维度分值决定,勋章级别越高(

在《仪礼》学发展史上,清代后期是一个以学术总结和转型著称的历史阶段。随着书院讲学的不断繁盛,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,传统文献刊刻事业的技术更新,民间礼学普及类读物的不断催生与渐次普及,晚清礼经学的传播与接受出现了新气象,较之《仪礼》文本的诠释与再诠释,显得更趋活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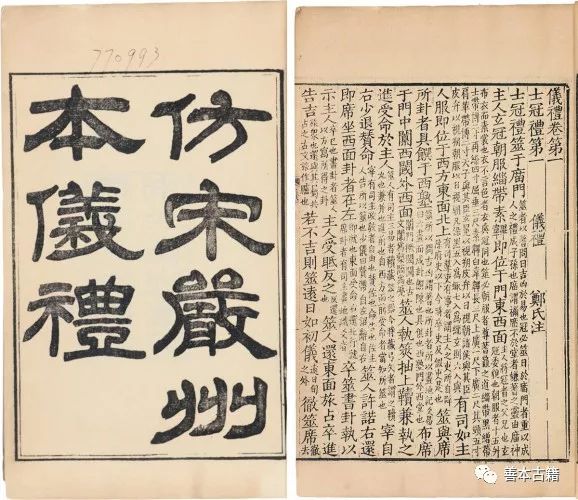
讨论清代《仪礼》学的演变与发展历史,尽管主要是围绕出现的各类清代《仪礼》文献开展研究,考察诸家学者关于《仪礼》的名物训诂和仪节仪制诠释等相关情况,辨析诸多流派的演变与发展脉络,但同时也要探讨《仪礼》学在具体现实社会的传播与接受情况。就清代后期而言,当学术史上的乾嘉时代过去之后,特别是历经了鸦片战争的社会动荡之后,整个社会虽然处于一个激烈变革的阶段,但就当时的学术潮流而言,学术界面临的现状是“传统仍固而西学已渐,经学复兴又新学蔚起”,经历着“‘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’和新的‘经世致用’的变化”[1]。对于《仪礼》学而言,也处于一个学术总结和转型期,在士人和社会群体中的传播,同样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。清代后期的《仪礼》学传播和发展,除了撰写专门论著的形式外,更多是和当时图书出版业的发展,以及各类学塾、书院盛行的讲学之风联系在一起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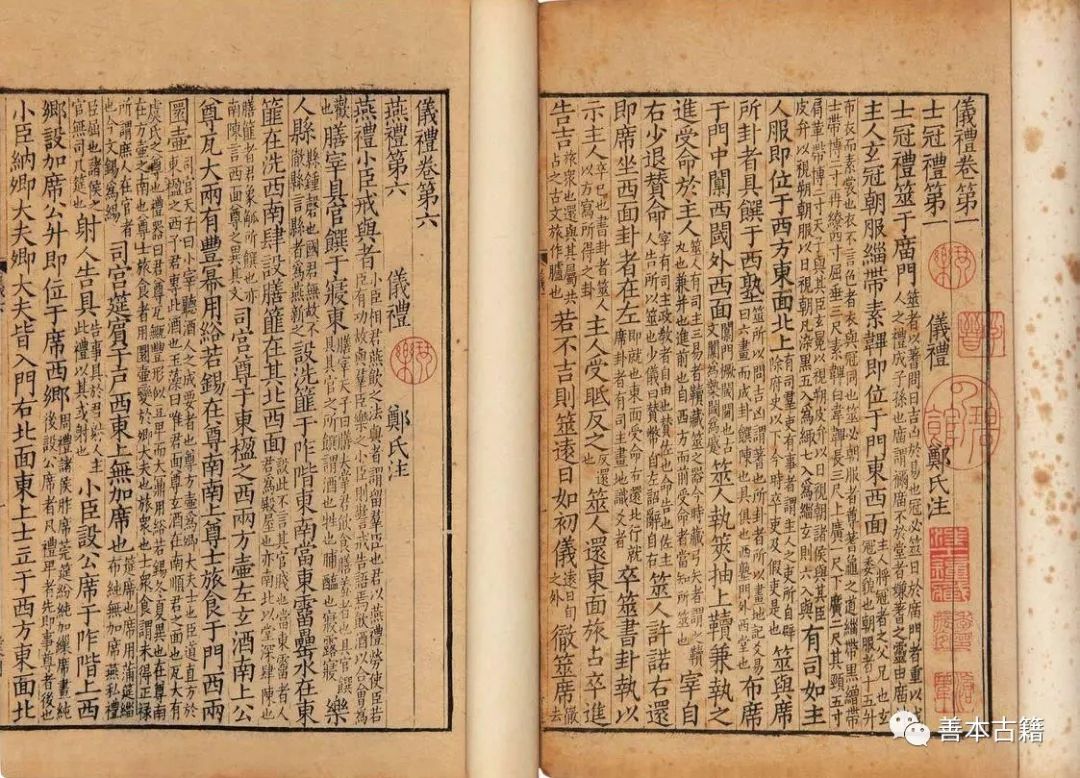
清代后期,出版界铅印和原有的雕刻并行于世,由于西方的平版石印和凸版铅印以及其他新技术、新设备不断传入我国,出版业的印刷更趋便利。较清代前、中期,此时所刊刻的各类经学文献定价更低廉,也较易得。加之当时南方一带战火连年,清政府国势日衰,民生凋敝,为了补充中损失的书籍,避免士人无书可读的凋敝现状,一些地方官员“提出‘及时振兴文教,刊刻成本’的主张,并且奏请把‘刊书’一事当做‘亟宜兴办’之要务”[2]。在他们的倡导之下,从官府刻书机构到书院所设书局,从私家刻书到民间坊刻,无不致力于各类文献的刊刻事业,包括《仪礼》学在内的各类经学文献,迎来了历史上的刊刻印刷黄金期,为礼学文化的普及和传播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。
清代前、中期的图书官刻工作主要集中在内府,然而到了嘉庆朝之后,武英殿刻书力量日渐衰落,殿本数量日趋减少,官家刻书的主体逐渐让位给各省的官书局。同治二年(1863年),曾国藩进入安庆,以振兴文化为名,创办官书局,并延请洪全奎、莫友芝二人督理创办书局事宜,选委一些积学名士分任校勘。后来曾国藩攻进金陵,又设江南书局。同治六年(1867年)二月,曾国藩二任两江总督,将书局正式命名为“金陵书局”。到第三年六月,曾国藩致信马新贻总督将原私立金陵书局转为官办。此后不久,各省专设的刻印机构——“书局”相继成立,主要包括:金陵官书局、浙江官书局、四川官书局、安徽敷文书局、山西官书局、山东官书局、直隶官书局等。这些官书局刻书,虽然所刊刻的书籍多是御纂、钦定的本子,但文献则以经史类著作为主,其中不乏《仪礼》学著作,业已成为清代后期地方官刻书的主要代表。例如:
同治七年(1868年),金陵官书局(后改称“江南书局”)刊刻有张尔岐《仪礼郑注句读》一书,系《十三经读本》之一种。光绪十二年(1886年),又重刻张氏此书。
同治十一年(1872年),山东官书局刊刻有张尔岐《仪礼郑注句读》一书,其中附《监本正误》一卷,《石本误字》一卷。
光绪三年(1877年),湖北崇文书局刊刻有胡承珙《仪礼古今文疏义》,一函四册。
光绪七年(1881年),江苏官书局刊刻有《读礼通考》一书。光绪年间,还刻有《仪礼注疏校勘记》《仪礼章句》四册等《仪礼》文献。
此外,浙江、山东、湖北、山西等地的地方官府刻书机构也刊刻了许多《仪礼》学著作。
这些地方官府刻书机构的成立和大量儒家经学文献的刊刻,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研究和传播,对于《仪礼》学的发展颇有裨益。此外,也有不少同样以“书局”命名的刻书机构,但并不属于地方官府机构所办书局,如苏州汤晋苑局、成都尊经书局等,都是书院下设的刻书机构,前者曾于同治七年(1868年)刊刻过《仪礼章句》二十册,后者则于光绪十六年(1890年)刊刻阮元《仪礼石经校刊记》一书,成为《石经汇函》本之一种。此类“书局”的成立与图书刊刻,为士人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精神食粮,使《仪礼》学的发展与传播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。
“书院刻书始于宋代,至清代为最兴盛,形成了古代刻书史上独树一帜的书院刻本”[1]13。清代后期,不少书院在从事传统的教育教学之外,还注重致力于刻书事业,借以保存国粹,振兴和传播传统文化,《仪礼》文献自然也在其刻书范畴之列。从清后期整个阶段来看,书院的《仪礼》文献刊刻,既有大部头的经学著作性质的刊刻,也有单独礼学著述文本的刊刻,更多呈现出一种于平淡中显露特色的态势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规模最大的两次丛书板刻和印书活动,依次如下:
一是补刊续刊学海堂“皇清经解”。该丛书始刻于道光五年(1825年),至道光九年(1829年),全书辑刻完毕,共收七十三家,一百八十三种著作,凡一千四百卷,是汇集儒家经学经解之大成,是对乾嘉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。咸丰七年(1857年),英军攻粤,原有书版遭受兵火的焚毁,残存者仅十之五六。咸丰十年(1860年),两广总督劳崇光等人捐资补刻数百卷,并增刻冯登府著作七种,计八卷,次年补刊完成,此即“咸丰庚申补刊本”。同治九年(1870年),广东巡抚李福泰刊其同里许鸿磐《尚书札记》四卷,附于“皇清经解”之后,是为“庚午续刊本”。
二是南菁书院编辑刊刻“皇清经解续编”。光绪十一年(1885年),王先谦以江苏学政身份主讲于南菁书院,延揽一批文人,收集乾嘉以后的经学名著,并及乾嘉以前为阮刻《皇清经解》所遗漏之书,依仿阮元《皇清经解》的编纂体例,统一加以汇编刊行。总计收书二百零九部计一千四百三十卷,作者多达一百一十三家。一直到光绪十四年(1888年),方刻毕刊行。该丛书所刊刻的清代《仪礼》文献主要有:江永《仪礼释宫增注》《仪礼释例》,任启运《天子肆献祼馈食礼》《朝庙宫室考》,宋绵初《释服》,胡培翚《仪礼正义》,吴卓信《丧礼经传约》,郑珍《仪礼私笺》,吴嘉宾《丧服汇通说》,曾国藩《读仪礼录》,俞樾《士昏礼对席图》《仪礼平议》。值得一提的是,丛书刊刻者在版本的选择与校勘上,下了一番功夫,如《仪礼正义》一书,胡培翚临终前并未完稿,余稿为门人杨大堉拾遗补成,咸丰初年由陆建瀛始加刊刻,业未就而陆氏罹难,版刻工作遂为停止,此后几经辗转,原板归于京师,胡、陆后人复于同治中方重加补校完成。初刊木犀香馆之汤晋苑局刻本,校勘未为精善,加之胡氏原稿多已散佚,无从订正,因而南菁书院“经解”重刊时,编辑校刻者对原刻本颇加校改,较之原刻本质量要高得多。
以上两套丛书的刊刻出版,称得上是集合了清代经学著作之大成,对于之后《仪礼》文献的传播,以及后人传承和总结包括《仪礼》学在内的清代经学成就,提供了极大便利。
另外,当时还有极少数学塾刊刻《仪礼》文献的情况出现,例如: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,东洲讲舍刊刻《湘绮楼丛书》,其中包括王闿运《礼经笺》一书。光绪十五年(1889年),雷浚应江苏布政使黄彭年之聘,任苏州学古堂主讲,和汪之昌一道纂辑《学古堂日记》,其中包括于鬯《读仪礼日记》和费祖芬《读仪礼日记》两种。
道光二十年(1840年)之后,清王朝进入急速衰落的时代,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到来和西方文化的侵袭,中国社会与传统的儒家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。尽管一部分仁人志士不满于汉宋学的空疏无益,主张关心民瘼,重新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,倡言社会改革,但也有不少学者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和儒家经学的传承,并且出现了一批以弘扬、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儒商、藏书家和刻书家。
相较于乾嘉时期而言,这一时期的私家所刊刻的《仪礼》文献数量不少,并以丛书本为主。从刻书者与文献著述者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看,清代后期刊刻的《仪礼》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:
刊刻自身及家族先人的著述。例如: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,朱氏家塾刻家族学者朱骏声所著《仪礼经注一隅》一书。同治八年(1869年),安徽绩溪胡肇昕重刻其曾祖父胡匡衷所著《仪礼释官》一书,该刻本有“同治己巳重刊”“研六阁藏版”等字样。光绪十四年(1888年),嘉定汤氏刻汤馥藻所著《仪礼指掌》一书。光绪十八年(1892年)及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,曹元弼先后自刻所著《礼经校释》一书。这种家族自刻族人所著礼书的现象,清代后期颇为普遍,有助于《仪礼》文献的及时传播,影响甚大。
刊刻乡贤的著述。例如,咸丰初年,安徽桐城光聪谐辑录同乡前辈著作一百余种,编成《龙眠丛书》。该丛书汇辑宋元以来龙眠文人之著述,而以清代为重,可惜锓版将成,即毁于兵火,刊未竣。今之所存仅二十二种,且亦残缺不全,其中礼学著作有方苞《仪礼析疑》一种。
刊刻时贤的著述。例如,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湘西李氏辅耀鞠园刊《读礼丛钞》。当其居其母徐氏之丧时,哀毁倍至,而动止必稽于古礼。既葬庐墓于长沙河西都绯珠塘,即墓为庐,名之曰怀翼庐,以寄其孺慕之思。复辑录有清理学名家张扬园、吴肃公、汪琬、毛奇龄、毛先舒、阎若璩、吴卓信、李文照、陈祖范、唐鉴、张华理、周保十二家说礼之书,别裁旁出,辑而刊之,命为《读礼丛钞》。
在道光年间之后私家刊刻的各类典籍当中,有的颇为精善,称得上善本之书,例如,吴江沈氏世楷堂所刊《昭代丛书》,便深受当时士人及后世学者嘉许。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,歙县学者张潮、张渐首先负责发起编辑该丛书,此后一直到道光年间,先后又经由吴江学者杨复吉增辑,沈懋德续辑,最终编纂完成。由于刊刻精善,所刻文献传播极广,颇受当时学者关注。
道光、咸丰年间,书院官学化程度不断深化,书院山长的延聘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。据光绪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三九六记载,道光十五年(1835年),道光皇帝下谕旨给各地官员:“延请院长,必须精择品学兼优之士,不得徇情滥荐。”为进一步强化书院的“育人”宗旨,突出山长的引领地位,朝廷重申山长人选的标准必须是“经明行修之士”,其聘请须经由教官、乡绅、耆老等共同推荐,以及地方官员认可才行。在朝廷发展文教、“底定人心”这一政策的指导下,在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,书院教育发展得以进入良性阶段。特别是在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丁宝桢、张之洞等一批地方军政大员的大力支持下,众多书院得到修复,新创建的各级各类书院数量也在不断增加,仅就数量而论便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。此后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光绪皇帝发布上谕,限定两个月内将全国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、西学的学校。至此,古老的书院在历经千年之后,终于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沉寂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。
考察书院教育在清代后期《仪礼》学的传播与接受情况,可以从两方面进行:一是礼学名家在书院讲学时期的文化传播情况,二是礼学名家经过书院学术熏陶的文化接受情况。当时社会活跃着一支周游于书院的讲学士子群体,他们一方面借以谋生,一方面通过课堂讲学、组织讨论、指导儒生等形式进行传道授业,传播自己的治学主张,并利用生活闲暇之余著书立说。这种情况在道光年间南方的一些省份表现尤为明显。在此种教育潮流之下,通过讲学、读经等形式,在师生之间进行儒学授受,包括《仪礼》学在内的儒家经学文化,在民间士人群体特别是儒生群体当中,得到广泛传播,并渐次加强了礼学研究人才的培养。据一系列个案考察发现,在清代后期有不少礼学家从事学术研究,都与在书院所受到的礼学、经学熏陶有着密切关联。
清代后期知名的朴学大师,俞樾毕生可谓与书院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,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教书授学,为清晚期经学、子学等诸多方面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很大贡献。道光十五年(1835年),其父在常州汪君樵家任私塾老师,他便随父读书,始得以粗通经文大义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至咸丰元年(1851年)间,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新安县汪村设馆教书。咸丰八年(1858年)侨寓苏州,始读高邮王氏父子《经义述闻》《广雅疏证》等书,遂发研经之志。是年秋,经江苏巡抚赵德辙引荐而主讲云间书院,授课之余,重读经书,旁及诸子,多有心得,以订正前人诂释谬误为乐。同治五年(1866年)秋,经两江总督李鸿章推荐,担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。同治七年(1868年),完成《群经平议》撰写并刊刻出版,并于该年冬天辞去紫阳书院教席,接受浙江巡抚马新贻邀请,任杭州诂经精舍主讲。同治九年(1870年)秋浙江省乡试中,诂经精舍学生中举者十九人,优贡三人,为历年所罕见,一时俞樾及书院声名大噪。光绪二年(1876年)夏,俞樾兼讲于上海求志书院,任经学和辞章学教授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冬,俞樾因年老辞去诂经精舍讲席之位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春,俞樾辞去归安龙湖书院和上海求志书院的讲席之位。俞樾在上述书院讲学经历中,尤以执掌杭州诂经精舍时间最长,从同治七年(1868年)至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达三十年之久。
俞樾长达几十年的书院讲学生涯,培养的各类学术人才无数。诚如有学者所言:“当时海内外慕名负笈来学者接踵而至,号称‘门秀三千’,投其门下者有戴望、朱一新、黄以周、章太炎、吴昌硕、施新华等人,对后世特别是对江浙地区之学术影响颇大。”[3]在执掌杭州诂经精舍期间,他谨守阮元讲学例规,不向士子传授八股时文的写作,“专课经义,即旁及词章,亦多收古体,不涉时趋。余频年执此以定月旦之评,选刻课艺,亦存此意。非敢爱古而薄今,盖精舍体例然也”[4]。在其讲学内容当中,经学讲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,他始终反对当时一些书院教学“以场屋应举、文诗课士”的做法,这从当时诂经精舍诸生的课艺之作中便能得到印证。
就《仪礼》研究而言,其书院弟子中影响最大者当属黄以周。黄氏问学“不拘汉宋门户,体亭林‘经学即理学’之训,上追孔门之遗言”[5]。黄氏著述《礼书通故》的学术旨趣,“并不在于资料的汇集编纂,而着眼于辨析是非,其资料的纂辑是服从于辨析是非的”[6]。这种强调辨析前贤治学是非得失的治学取向,与俞樾《群经平议》的治学形式虽有所差异,但治学要旨是一脉相承的。他的礼学研究也赢得了俞樾的赏识,如俞樾以为秦蕙田《五礼通考》“按而不断,无所折衷,可谓礼学之渊薮,而未足为治礼者之艺极”,而肯定黄氏著述《礼书通故》虽然“视秦氏《五礼通考》博或不及”,但“精则过之”[7]。
在俞樾的书院弟子中,研究《仪礼》较有成绩者,还有上海南汇人于鬯。他一生致力于经史之学研究,对于儒家“五经”都有遍览和刊正之作,其中与《仪礼》学密切相关者,主要有《读仪礼日记》《仪礼读异》《殇服》《香草校书》数种。于鬯谈及自身问学旨趣时说:“阮氏元叙程书曰:‘夫玩索经之全文,以求经之义,不为《传》《注》所拘牵,此儒者之所以通也。’鬯谓阮氏此言,可为读书之准。此非不讲师承也,乃正善于讲师承也。所恶于异郑者,为其师心自用、违经背理也。若本经以为义,则又何恶?且郑君之学惟不专主一家,故能成其大。今学郑而惟郑之是,不适坏郑氏之家法乎?必非郑君所许矣。”[8]强调既要遵守郑氏治礼家法,又反对一味唯郑《注》是从,一切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准则,这也与俞樾所说“著每遇一题,必有独得之见,其引前人成说,或数百言,或千余言,要皆以证成吾说,合吾说者,吾从之,不合吾说者,吾辨之、较之,而非徒袭前人之说以为说也”[4]的治学要旨,是大体相吻合的。
再如,江苏阳湖(今属常州)学者蒋彤研治礼经,也受他的同乡、书院师长李兆洛治学影响很深。李兆洛,字申耆,号绅琦,晚号养一老人。嘉庆十年(1805年)进士,改庶吉士,授安徽风台县知县,兼理寿州。后奉讳去官,先后主讲真儒、敬敷及江阴暨阳书院,前后将近二十年。薛子衡《养一李先生行状》记载李氏:“日聚弟子讲诵其中迨十余年,而暨阳科第之盛倍于往昔,治经术、通音均、习训诂、订与图、考天官历术及成学治古文辞者辈出,皆先生所授也。”他学识宏富博通,对于汉唐以来诸儒有关儒家“十三经”文献及成说颇有娴熟,而且好学深思,“期为有用,异于守一家之言、立帜以焉名高者”,“士通一艺,咸思罗致,后进咸奉为依归”[9]。
李兆洛教学颇有方法,“先生因材而教,使治经术,通音韵训诂,订与图,考天官历算,及治古文辞,各专一艺,成就者辈出”[9]。在暨阳书院主讲期间,他一边教学一边著述、刻书,而且多能得到书院之众弟子相助,“此间诸子甚有向学者,析疑求是,差用欢然,以乐慆忧,聊堪遣日”[10]。在众多相与帮助的书院生徒中,蒋彤是最受李氏欣赏器重的一位弟子,他将平时讲学与师生交流的言论记载下来,在李氏死后整理成册,即《暨阳答问》一书。张舜徽先生在谈到蒋彤治学情况时,曾作如是评价:“彤之为学,承兆洛遗风,主博综而蔑据守,不期以专门名家……其于经史实学,颇有根柢。”[11]
受李氏影响,蒋彤“涉猎诸子,精于礼学,在《暨阳答问》中已有呈现。而此种学术兴趣,皆有李兆洛的导引之功”[12]。礼经学方面,蒋彤专力于《丧服》篇的研究。李兆洛曾就其《丧服》研究指导说:“先生谓丹棱曰,人学问须使有归聚处。汝既学《丧服》,大旨已得,便可搁过,但认真读书讲论,义理归到《丧服》一路上去,越归越多,越熟越精纯,超国朝追六朝人,且直接周公、孔子,若急欲成书,其有难通处,且将附会穿凿,自家回护其说,便做成郝敬、敖继公一派。汝今驳辨诸家,动不合己,岂知他成此书时,亦皆极力辩驳,矜为独得之秘耶?独得之秘亦何足恃,汝果能尽得天理人心之安耶?”[13]受此言论影响,蒋彤所著《丧服表》《集传》诸书,均不以“驳辨诸家”说解为治学之要旨,更多呈现出“承兆洛遗风,主博综而蔑据守”的特点。
上述诸位礼学家或于书院通过讲学形式传播礼学文化知识、培养礼学研究人才,或通过进入书院接受经学名家的教育,致力于推进礼经文化的传播与接受,使得礼学研究代不乏人,意义和影响甚大。此外,还有不少礼学名家借助书院讲学和研修,衍生出一批礼经学著作。例如,江苏山阳学者丁晏,在阮元延聘江藩主讲于丽正书院时,系丽正书院的一名生徒,接受了正统的汉学教育,后其亦主讲该书院,著有《三礼释注》八卷,成为株守郑学派的一位急先锋;皮锡瑞曾主讲江西经训书院;朱骏声早年肄业紫阳书院,后主讲江阴、吴江、荆溪、萧山等书院;郑珍先后主讲于湘川、启秀书院;胡培翚先后主讲于钟山、惜阴、云间、泾川等书院;张锡恭肄业于南菁书院等等。他们的礼学研究无不被打院礼学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烙印,着实令人注目。
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,《仪礼》蕴含着西周圣贤理想中的思想价值体系,同时又承载着汉代以来民众日常行为处事、伦理教化所需要的社会价值取向。清代社会对于礼经的文化传承,不仅仅通过各式各样的学术研究体现出来,同样也会借由民间儒生编纂的各类童蒙读物得以推广开来。诚如陈来先生所说:“在中国文化中,中下层儒者实施的蒙学教育才是伦理教化的直接活动。”[14]对于礼学文化而言,礼学不仅仅是曲高和寡的精英文化,同时也是一种“化民成俗”的实践性很强的大众文化,必然会借由民间儒生传播延伸到乡村蒙学领域,从而推动“三礼”文化的进一步推广,催生一批普及性较强的礼学读物。
道光十五年(1835年),山西太谷学者孟先颖著《仪礼问津》。他在“自序”中称:“我朝《仪礼义疏》一书,举汉、唐以来难端疑义,阐发晓畅,足以息诸家聚讼之纷,而本经之难读依然,后生小学终不免望洋思返。吾师孔舟山先生向有手抄本,以便生徒记诵。其章段解说,以《注疏》为宗,兹复本《义疏》抄录,别为一编,经岁脱稿,同人借抄者踵至,已不仅为家塾课本,恐四羊三豕,点化成讹,转致贻误后学,爰重校付梓,用代传抄,名之曰《仪礼问津》,盖于望洋思返之下,以求一苇之航尔云云。太谷孟先颖识。”[15]可见,该书亦为一部读本体著作,“于经文皆分章段,所引诸家论说,不标姓氏,而于‘御案’则特圈出,旨在实用,于初学讲诵相宜”[16]。
道光后期,江苏元和(今苏州)学者朱骏声著《仪礼经注一隅》两卷。朱氏自作《弁言》说:“昌黎博敏,犹苦难读。与其不读,毋慭屚略。僮蒙犬子性非颖,特全经之授虑艰上口,强涩记诵,耗积时日,妄率己意,断章节,取经、《记》、《注》、《疏》一隅,是举聊为塾课。”[17]朱氏引经文颇不规范,不求全而重贯通,因此许多篇目的经、《记》都是经过删节而成的;朱氏还特别运用串解体的编排方式,通过增添少量相应的文字,贯串经文之意,使经文成为浅显易读的文字材料,则该书纯为塾课而撰,不重在学术创新。书中收录《仪礼》十七篇并不完整,其中《丧服》《士丧礼》《既夕礼》《士虞礼》四篇有目无文,《士相见礼》篇经文也仅止于“若有将食者,则俟君之食然后食”一句。经过朱氏行文串解之后,整段文字几近于大白话,颇利于塾课之易。
同治后期,河南祥符(今开封)学者刘曾著有《仪礼可读》《仪礼约解》。刘曾重视蒙学,其于“三礼”类著述有《周礼可读》六卷、《周官约解》三十五卷、《仪礼可读》十七卷、《仪礼约解》二十三卷、《礼记可读》八卷、《礼记约解》三十六卷等,均属于读本体著作,传统儒学启蒙教材特色较为明显,现有光绪间《祥符刘氏丛书》油印本传世。其中《仪礼可读》大致缀取各篇仪节大要而成,自谓“韩昌黎读《仪礼》曰:‘缀其大要,奇辞奥旨著于篇,学者可观焉。’惜其书不传,兹编乃仿而为之”[18];而《仪礼约解》则不详载《仪礼》十七篇经文,只取所需约解的经文文句,并摘引前贤时哲有关研究成果为之约解,至于诸儒考辨疏证过程性质的语段一概不收入该书,著述不求广征博引,务求明经义而已。
光绪十四年(1888年),上海嘉定人汤馥藻刻《仪礼易读指掌》一书。据汤氏《自序》称,光绪十二年(1886年)冬,汤馥藻“得山阴马氏《仪礼易读》一书,用注文以衬明经文,其义明矣,惜乎全书仍难以卒读也。又得长沙唐陶山先生《仪礼蒙求》一书,一礼为一篇,简则简矣,骤而观之,亦仍不甚明了,因取《易读》合观之,方知某字为某句所由出,某句为某节所自来,且其例无郑《注》、贾《疏》一字入文,故间有拘泥于经文而反致词晦,牵强于对仗而转成语病者,非加注释不明也”。基于此,汤氏取唐陶山所著《仪礼蒙求》十二篇“隐者显之,晦者明之,奥者达之,繁者删之,略者益之,俾读者至明且易,如示诸掌,名曰《指掌》”[19]。该书共分十三卷,每卷分上下篇,上篇为《仪礼易读》,下篇为《仪礼指掌》,依《仪礼》十七篇次第,一礼为一篇,惟缺《丧服》《士丧礼》《既夕礼》《士虞礼》未刻。其中《仪礼指掌》是在唐陶山《仪礼蒙求》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。于每页上方又加附注语,有时亦取聂崇义《三礼图》中《仪礼》诸图列于上方,引《注疏》精义细绎之。每一节之首略用提笔,一节之尾略用收笔,以清眉目。据此可见,该书的编刻,对于《仪礼》的普及推广,确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。
光绪年间,湖北钟祥学者黄元善著有《仪礼纂要》。黄氏作《仪礼汇编引》云:“兹就坊刻《约编》揭要经注,诸选本所已采入者辑存之,复于经、《记》中摘增万千数百字,共一万九千八百余字。其细注、旁注、顶批、反切,俱遵《仪礼音训》《仪礼注疏》及《钦定仪礼义疏》汇入。至卜氏丧礼一册,为《公》《谷》所自祖,照录原文不遗一字。每编仍录《约编》‘叙略’缀于其后,使读者一目了然,易于成诵。”[20]可见,黄氏该书主要根据《仪礼约编》《仪礼音训》《仪礼注疏》及《钦定仪礼义疏》等删节而成,是一部删改体著作,注释甚为简明。通观黄氏全书,《士冠礼》至《觐礼》“经、《记》择读”,《丧服》篇“全读”,《士丧礼》《既夕礼》两篇阙,《士虞礼》篇“经阙录《记》”,《特牲馈食礼》《少牢馈食礼》及《有司彻》三篇“经、《记》择读”。
总之,清后期一部分礼学家纷纷将研究视线转移到《仪礼》文化的普及中来,从事于课蒙读物著述编撰的工作。尽管此类礼学著作大多缺乏创新性,但对于《仪礼》学在民间士人群体和童蒙当中的推广与普及,却发挥着专门论著难以企及的作用。就此间《仪礼》普及读物著述体式的选择情况来看,不仅有清中期礼学家所选择的“读本体”“删改体”两种编纂方式,又有少数学者另起炉灶,尝试用增串体、评点体的著述方式。读本体著作主要有《仪礼抄略》《仪礼便蒙》《读仪礼录》《仪礼约解》《仪礼可读》《仪礼先易》《仪礼问津》等几种,删改体著作则有《仪礼注疏删翼》《仪礼纂要》两种,增串体著作有《仪礼经注一隅》一种,评点体著作有《仪礼评点》一种。在清后期成书的《仪礼》文献当中,普及读物比例已经占四分之一左右。这是清代前期与中期所难以比拟的,着实彰显出后期《仪礼》文化的普及与传播之盛在民间的影响之深。
[1]胡昭曦.振兴近代蜀学的尊经书院[M]//蜀学(第3辑).成都:巴蜀书社,2008.
[2]张雪琴.从浚文书局到山西书局——近代至民国时期的山西图书出版业[J].新闻出版交流,2003(5).
[3]苏菡丽.俞樾的经学思想及其特点[M]//东吴哲学(2006年).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07.
[4]〔清〕俞樾.诂经精舍五集序[O]//春在堂杂文六编(卷七).光绪二十五年重订本.
[5]支伟成.清代朴学大师列传[M].长沙:岳麓书社,1998.
[6]王文锦.点校前言[M]//礼书通故(卷首)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
[7]〔清〕俞樾.礼书通故序[M]//礼书通故(卷首)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
[8]〔清〕于鬯.读仪礼日记[O]//续修四库全书(第93册).影印清道光二十九年朱氏家塾刻本.
[9]〔清〕徐世昌著,舒大刚等校点.清儒学案(卷一百二十七[)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0.
[10]〔清〕李兆洛.又寄钱大今[O]//养一斋文集(卷八).光绪四年刻本。
[11]张舜徽.清人文集别录[M]//张舜徽集.武汉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.
[12]徐雁平.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[M].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7.
[13]〔清〕蒋彤.暨阳答问(卷四)[O].道光二十二年木活字本.
[14]陈来.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3.
[15]〔清〕孟先颖.仪礼问津序[M]//三礼研究论著提要.兰州:甘肃教育出版社,2001.
[16]王锷.三礼研究论著提要[M].兰州:甘肃教育出版社,2001.
[17]〔清〕朱骏声.刻《仪礼经注一隅》弁言[O]//续修四库全书(第93册).影印清道光二十九年朱氏家塾刻本.
[18]〔清〕刘曾.仪礼可读[O]//祥符刘氏丛书.光绪元年油印本.
[19]〔清〕汤馥藻.仪礼指掌·自序[O]//仪礼易读指掌.光绪十四年家刻本.
[20]〔清〕黄元善.仪礼汇编引[O]//仪礼纂要.光绪二十年刊传经书屋藏本.
推荐内容
为您推荐
简短上档次的姐姐结婚祝福语18条【精选】
祝福语是指对人们的美好祝福的语句。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简短上档次的姐姐结婚祝福语18条,仅供参考,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。
2023-11-11 08:19:03
精品文章
热门推荐
大家都在看
- 穿越之众夫宠妻 月光舞鞋|一年级月光舞会? 一年级不再见:月光舞会变结婚纪念日?
- [对新人的祝福语高雅的简短]对新人的祝福语高雅的
- [伴郎伴娘微信群名称]伴娘团群名称
- [简短新婚祝福语八个字结婚祝福语]结婚祝福语一句:金婚祝福语:简短的结
- 情侣之间的爱称创意|情侣之间的爱称
- 人生没有回头路的名言|人生没有回头路说得太有道理了!
- [感谢词语简短]感谢词语
- 关于白头偕老的结婚祝福语【三篇】
- 浪漫爱情故事长篇暖心_浪漫爱情故事
- 【澳洲结婚移民流程】澳洲移民流程-快速了解澳洲移民的流程
- [结婚典礼证婚人台词]结婚典礼主持人的台词
- 【微博渡边淳翼】渡边淳一语录
- 【后悔句子大全经典励志】表达很后悔的经典句子
- 新婚祝福语简短上档次_新婚祝福语简短
- 人生没有回头路的名言|人生没有回头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必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